《南鄉子·搗衣》鑒賞
原文
鴛瓦已新霜,欲寄寒衣轉自傷。見說征夫容易瘦,端相。夢里回時仔細量。
支枕怯空房,且拭清砧就月光。已是深秋兼獨夜,凄涼。月到西南更斷腸。
賞析
該詞以怨婦的口吻,描寫主人公的“自傷”、“怯空房”、“凄涼”,以至“斷腸”的怨恨之情。全詞層層寫來,情致幽婉凄絕。古時搗衣,多在秋夜進行,試想一下,在一個寒冷的夜晚,四下悄無聲息,只能聽見蕭瑟的砧杵聲一下一下地響起,這是何等凄涼的意境。因此,在古典詩詞中,搗衣往往用來表現征人離婦、遠別故鄉的惆悵情緒,而在這首詞中,納蘭正是借搗衣這一動作,抒發了征夫怨婦的相思情懷。
詞的上片,集中描繪思婦搗衣之苦情。整個上片,全以“秋聲”來渲染烘托思婦心中之哀苦。“鴛瓦已新霜,欲寄寒衣轉自傷”,詞一開篇,作者就交代了時令,天氣逐漸變涼,鴛鴦瓦上已經落滿了秋霜,此時的思婦想要為遠方的征人寄去寒衣,卻又突然開始暗自傷懷。一個“轉”字,說明婦人先前的心情并非“自傷”,但是一想到這砧板上的衣服是為遠行在外的征人而搗,自然睹物思人,心中已是思念不已。“見說征夫容易瘦,端相,夢里回時仔細量”,在這里,納蘭想象著思婦懷念征夫時所流露出的纖細感情:都說出門在外的人容易消瘦,不知道是否是真的,下次在夢里相見的時候一定要好好端詳端詳你。在納蘭所寫的詞作中,他不僅用種種的具體事物來表達抽象的戀情,更多的時候是通過這種虛幻的夢境來表達揮之不去的思念。你聽,有受驚鴻雁的凄涼哀鳴,有滿階落葉沙沙的飄響,有夜半二更的更鼓聲響,有蕭瑟生寒的西風呼嘯。這一切在靜夜傳響,聲聲真切,真是縱有“西風吹不斷”。如此環境氛圍,思婦倍加凄苦孤單、倍加凄切傷心,更有甚者,在這凄苦的秋聲中,還要加上自己不停的搗衣聲。一聲聲飽含著自己的凄苦辛酸,一聲聲寄寓著對丈夫的思念和關切,正所謂“中有深閨萬里情”。
下片形象地描繪兩地相思的情境。因為思婦獨守空房,既倍感寂寞,也不免會心生膽怯,無奈之下,思婦只好通過在月光下擦拭搗衣之石來消磨時光。而此時“已是深秋兼獨夜”,深秋獨夜里,寒月、寒砧,伴隨著一顆孤獨寂寞的心,詞到此處,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一個讓人憐惜、同情的思婦形象躍然紙上。尾句“月到西南更斷腸”,進一步描寫思婦內心中的相思愁苦。夜已經深了,又要與寂寞孤獨相伴,連月亮都要落下了,怎能不叫我傷心斷腸。納蘭的這首思婦詞寫出了滿紙的凄苦,可謂是一首“斷腸“之作。“片石”兩句承上,先寫搗衣之后,夜深、石冷、霜凝之狀,可見思婦是長久地沉浸在對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,如癡如果。“今夜”以下,是轉寫征夫歸夢,今夜遠戍邊關之人定會在鄉思的歸夢中,分明看到妻子頻呵著纖纖雙手帶月前迎國。當然,也可解作夢見丈夫歸來,自己呵手出迎。兩地相思一樣情,這種夢幻中的相會是夫婦雙方的期盼,是他們遙相思念的心靈感應。
全詞平實如話,但卻深情情韻。細細讀來,如聞酸楚凄涼的搗衣之聲。如見夢中相會的具體情景,也可體味出作者對遠遣之友的深切同情。令人讀罷不禁嘆息欺欷,一掬同情之淚。
納蘭性德簡介
唐代·納蘭性德的簡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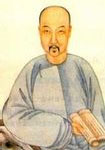
納蘭性德(1655-1685),滿洲人,字容若,號楞伽山人,清代最著名詞人之一。其詩詞“納蘭詞”在清代以至整個中國詞壇上都享有很高的聲譽,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光采奪目的一席。他生活于滿漢融合時期,其貴族家庭興衰具有關聯于王朝國事的典型性。雖侍從帝王,卻向往經歷平淡。特殊的生活環境背景,加之個人的超逸才華,使其詩詞創作呈現出獨特的個性和鮮明的藝術風格。流傳至今的《木蘭花令·擬古決絕詞》——“人生若只如初見,何事秋風悲畫扇?等閑變卻故人心,卻道故人心易變。”富于意境,是其眾多代表作之一。
...〔 〕